拯救那些“孤独”的孩子 <自闭症治疗>
为什么会这样?这并不意味着自闭症的“发病率”在迅速增加,而很可能只是“检出率”大大增加了。中国人的科学育儿意识是最近10年才爆发的,早教课程相对普及也才五六年;没有家长的知识储备和警惕性,不容易“诊断”出自闭症。可想而知,无数的孩子被家长和社会当成了“疯子”和“傻子”,尤其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。
谁知道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?除了盲目无序的治疗,正规机构进行的正规治疗,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也会收效甚微。京华四大校区——顺义、安贞、天通苑、高碑店的七彩鹿每天人满为患,每年为差不多一万名患者提供服务;与排队上课的患者相比,“一万”只是九牛一毛。
十几年前,被父母锁在家里的孩子偶尔会出现在电视节目中。虽然无法检测,但他们很可能是重度自闭症的受害者,但当时周围的人并不知情,大众只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猎奇的谈资。
第三个错误体现在“自闭症就是天才”之类的刻板印象中。有些人经常谈论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。阿斯伯格综合症是自闭症的一种轻度形式。虽然它也伴随着社交障碍、沉默寡言和刻板行为,但它不会带来精神和语言障碍。儿童往往可以作为一个“有点古怪”的人站在社会上,有些人甚至可以成为伟人,如漫画家朱德庸。
但是,开颅手术并不是无知的全部。媒体关于自闭症的报道血淋淋的。为了纠正自闭症儿童的刻板行为,一些机构使用暴力殴打,将他们变成“不敢说话或移动的木头脑袋”,并声称自己是成功的。有的机构认为自闭症孩子精力旺盛,就穿上棉衣跑步,声称在孩子筋疲力尽后“让孩子冷静下来”。至于各种电击,倒挂,扎针,注射毒品,不胜枚举。
这是一个给自闭症儿童的区域,七彩鹿,一个在残联角落的自闭症康复机构。这里挺吵的,但是空气中充满了压迫感。这里不缺人,但却远离世人的关注。甚至禁止拍照。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调的自闭症干预,这已经成为语言上的禁忌。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如此频繁,但很少有人愿意跳出来把自己当标本。一个孩子被老师反复问“你刚才喝水了吗?你喝水了吗?刚才该喝水了。我们应该喝水吗?然后,孩子什么也没说,拿起水杯又喝了一口,直到被同学打断——一个看似开朗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说:“老师,刚才我看见他在喝水。"老师耐心地继续问,"你喝水了吗?喝完酒怎么不说?这是自闭症儿童常见的状态之一。如果说一些普通人缺乏社交能力的话,自闭症患者根本就缺乏社交的意愿和能力。他宁愿再喝水,也不愿告诉老师“我受够了”。
这是第二个错误。就像“孩子被链子拴住”一样,如果父母认真带孩子就医,亲戚邻居就会开始造谣:“那谁家生了个傻子!这种压力无疑会让患者的家庭更快崩溃。在朝阳区残联四楼,我遇到的很多家长都是“背着家人来的”,尤其是“背着爷爷奶奶来的”,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家人的质疑了。
然而,这是20年前的结论。
他们应该提高教师的待遇,纠正家长的观念;他们要尽力覆盖患病儿童,也要想想对成年自闭症患者的关心;他们在努力走出北京,他们也在努力走出国门……我对孙梦麟说: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企业能完成的事情。马先生补充道:即使现在所有的从业者加起来,也远远不够。
这家位于朝阳区残联四楼的康复机构,名叫彩鹿,是国内最大的相关机构之一。成立于2005年,听起来是个“老企业”。但鉴于行业的特殊性,相对于当今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速度,七彩鹿被称为初创企业并不为过。
之后直到2006年,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才参考国际标准,将自闭症纳入精神残疾范畴。而一个知名医院支持的大型机构,比如北大医学儿童发展中心,你猜是哪年成立的?答案是2015年。别忘了它只位于北京。
但对于服务自闭症患者(也称“自闭症”)来说,情况并非如此。你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。你离他们越近,你就觉得离他们越远。工作时间越长,接触的自闭症患者越多,你就越感到孤独,他们甚至比你更孤独。关键是,这种孤独可能永远不会结束。
孙梦麟算了这样一笔账:自闭症教师上岗,首先需要专业对口,然后需要两个月的脱产培训。经过脱产培训,需要一年左右的实践,才能独立工作,创造效益。教育自闭症儿童工作量大,心理压力大,但并不是光鲜亮丽,地位高的职业。与教钢琴和绘画的美术老师相比,他们的收入绝不算高。
那个时候,孙梦麟除了时间和金钱,一无所有。中国自闭症人才少。例如,杨小玲等专家愿意为彩鹿提供有限的支持,但他们无法投身于一家创业公司。在这样一个连路都找不到的环境里,彩鹿怎么起步?用孙梦琳的话说,她很“幸运”,赶上了两场会议。这两次会议使她能够会见必要的合作伙伴和最初的客户。2005年底,国际行为分析协会(ABA International)第三届年会在北京召开(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意大利和巴西召开)。行为分析(ABA)与自闭症的诊断和干预密切相关,所以孙梦琳认识了以色列ABA专家覃逸·艾德博士,他将在未来为彩鹿带来巨大的帮助。也是在这几天,孙梦麟认识了美国皇后学院的王教授。
埃德博士是以色列ABA协会的第一任主席。他有自己的研究所,领导着一支专业的自闭症康复训练团队。王教授就职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,博士级应用行为分析治疗师。第二,人们对自闭症治疗的社会价值有了很好的认识,学术研究也渴望中国自闭症群体的海量数据。他们和孙梦琳很合得来。
这些年来,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自闭症孩子做开颅手术,已经做了三四次了。孩子受了很多苦,自闭症根本不会好起来。孙梦琳无奈地说,来彩鹿的孩子很多都做过开颅手术,这是因为家长的焦虑和无良机构的欺骗。
举一个第一个错误的例子——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有自闭症病例是如何被发现的?当然,少数非常认真负责的家长可以在孩子几个月大或者至少3岁之前发现孩子的异常,但更多的家长对自闭症的认知是非常被动的。具体来说,当他们的孩子在该上幼儿园的时候上不了幼儿园(面试失败或者被勒令退学),在该上小学的时候上不了小学,他们就会意识到“我的孩子有问题”。这让我想起了《流浪者》里钟娟养小次郎的故事:都养出了感情,却还没发现孩子聋了。
我曾经热衷于成为一名志愿者,我也热衷于与其他志愿者交流。志愿者帮助别人,他们得到安慰。虽然志愿服务的场景并不总是美好的,更多时候甚至是令人心寒的,但是老人会去仙,孤儿会长大,很多苦难会走到尽头。
注意是收入的10%,不是利润的10%,而且是收入而不是净收入。如果你同意这个条件,就意味着艾德是真正的老板,包括孙梦麟在内的所有彩鹿都将为他效力。
但是孩子比天还大,全世界都一样。上面提到的两次会议中的第二次是在广州举行的非正式会议,许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都出席了会议。当时彩鹿刚刚成立,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自闭症康复机构。很多家长听说彩鹿的事情后,马上找到孙梦琳预约。他们从广州北上北京治疗,与北医六院专家推荐的患者一起,构成了彩鹿的“种子客户”。
作为一个企业的七彩鹿,12年能自给自足开4个校区,治疗10多万患者,足以说明这个领域的商业价值。要扭转自闭症治疗供需极度失衡的局面,商业化是必由之路,这也是近两年彩鹿像“初创企业”一样开始融资的原因之一。事实上,互联网圈的投资人参与自闭症相关项目由来已久,“恩启云课堂”就是成果之一。
简而言之,父母希望孩子“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”;就算带孩子参加治疗,也只是希望孩子该上中学的时候能上中学,该工作的时候能挣钱。这个简单的愿望可以理解,但是自闭症干预的黄金时间是在8岁之前,14岁之后的干预基本没用。越早主动发现越好治疗,这种“被动发现”耽误了很多人。
然而,他们加入中国的创业公司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ed开出了相当高的条件,比如月薪1万美元(在2005年绝不低),比如住五星级酒店并由公司报销,比如Ed获得公司总收入的10%。
说自闭症是先天性的是有道理的。哪怕是被动,哪怕是后知后觉,孩子进入幼儿园就应该发现他的异常。之所以还是耽误了太多人,一是有的孩子病情有轻有重,有的孩子中学时的异常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;第二,由于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病有嫉妒心,即使发现了,也往往抱着“侥幸心理”去拖延,最终导致不好的结果。
果不其然,当我步出电梯,进入四楼,一波又一波的声音开始冲击我的耳膜:幼童的啼哭,中年人的指令,年轻女性的呵护,还有不知名人士无尽的低语。我环顾四周,满地都是孩子,老师到处都是,家长都低着头坐在椅子上。
今天的情况当然好了,但是大部分家长还是没有正确的态度,整个社会对自闭症充满了误解。
来到朝阳区残联,整栋楼静得可怕。马老师告诉我,这里除了四楼,人不多。
孙梦麟表示,要想从根本上为广大自闭症患者提供充足的医疗保障,就必须提高员工的待遇。这也是彩鹿的长远目标之一。所以很容易理解,在自闭症干预领域,即使著名的星雨成立较早,NGO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非常有限的。
自闭症儿童往往会出现反复症状,这让教育者的成就感受挫。在孩子背后蹦一万次,可能都让他记住了自己的名字。但是当你某天早上醒来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,他的反应可能突然就跟一年前一样了。孩子能站着不动,家长怎么能回到一年前的心态,怎么能把这一年当成什么都不是?
我确实在残联四楼看到了很多白人孩子和白人家长。客观来说,全世界有很多声称提供自闭症治疗服务的机构,但它们是什么呢?
我在七彩鹿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小胖子。他的自闭症长期得不到治愈,所以被父母抛弃,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老人的家教水平对干预自闭症无能为力,孩子的病情经常反复。即使老师们都在身边,天天陪他睡觉,得到的也只是攻击的抓痕。这个孩子的刻板行为体现在暴饮暴食上,让他的外表看起来“异常”——其实在父母抛弃他之前,他并不肥胖。
马老师带我去见一个教员。小伙子静静的坐在角落里剪彩纸,我们走近却没有任何反应。马先生打电话给他,把我介绍给他。他对我说,“你好。马先生问他:“你在干什么?他说:“我在做教具。当我们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,马老师说:“干预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,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个体。我们的目标是让自闭症患者能够融入社会,或者至少能够独立谋生。虽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做到。”“像他这样的人很少。马老师回头看了看剪教具的年轻工人。
自闭症怎么能等同于愚蠢呢?从外表上看,自闭症儿童与唐氏综合征(或21-三体综合征,很多人应该在生物课本上见过)儿童有明显区别,所以根本不应该混淆。然而,正常的外表使自闭症更难被诊断。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自闭症患者家庭的毁灭是现实的,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正规的干预机构不仅要为自闭症儿童开展各种课程,还不会忘记对家长心理健康的辅导。如果家长不关心和配合,仅靠老师是很难达到治疗目标的。
作为一家康复机构,彩鹿12年治疗的患者超过10万人,已经做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自闭症病例数据库,让他们在学术界声名鹊起。从去年开始,他们做好人脉,招募技术人才,希望以“平台”的形式,将事业从线下拓展到线上:从对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干预,到包括家长远程指导在内的“全家支持”,再到自闭症患者生活的“全程支持”,也就是说,完成对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救助。
七彩鹿创始人孙梦麟之前的工作是家庭主妇。因为家庭环境比较富裕,孙梦麟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。她儿子上初中的时候,他们已经去过几十个国家了。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,孙梦琳结识了北医六院自闭症专家杨小玲教授,并逐渐进入这个圈子,最终于2005年成立了彩鹿。
12年来,孙梦麟在国内外旅行,在医生、学者、志愿者和官员之间建立共识。他们赢得了残联的会场和在各大协会的话语权。如果不传播正确的思想,仍然会有孩子遭受毫无意义的开颅手术,也会有“疯子”像狗一样被绑在农村的院子里。
当家长在正规机构为自闭症孩子寻求“出路”时,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“目前自闭症无药可治”。
与常见的误解不同,自闭症不是抑郁和焦虑。大多数情况下,不需要吃药,但也缺乏治愈。正如马老师所说,“目标是让自闭症患者能够融入社会,或者至少能够自食其力”,而不是“一劳永逸”。千万不要因为治不好就认为早期干预无关紧要。科学干预可以改变自闭症儿童的生活,让他们“更有质量地”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。
当然,有些孩子死于非人待遇。但是,即使取缔了非法机构,也没有给孩子和家长带来新的希望。即使在正规机构,无药可救,长期的治疗,高昂的费用,都在摧残父母的心。
与美国和日本相比,中国的自闭症干预起步相对较晚。1982年(美国早在1943年就确诊了),mainland China确诊了第一例自闭症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当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杨小玲等几位专家开始研究时,他们手中只有30个病例。从1993年开始,星星雨等私立康复机构陆续成立,自闭症家庭陆续有了“去处”,尽管很多时候只能寻求慰藉。
同样,虽然自闭症被国家认定为精神残疾,每月有2600元的补助,但真正会领到这2600元的家长并不多,因为领到的前提是办理残疾。用一位家长的话来说,一旦得了残疾,无疑会给自闭症增加一个“终身创伤”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是“残疾人”。
然而,让父母崩溃的不仅仅是无药可救的尴尬,还有高昂的治疗费用。在美国,自闭症干预教育一年的费用是7万到12万美元,远远超过大学学费,根本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的。虽然彩鹿提供的专业治疗比美国便宜很多,但考虑到中国父母的收入,还是一个沉重的压力。
在开始治疗孩子的自闭症后,很多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:“我要离婚。我怎么和他/她生了这样的事?”这听起来很可怕,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。2016年春节前夕,湖北一父亲勒死5岁自闭症儿子后投案自首。他痛哭流涕,他全家都痛哭流涕,但孩子已经被他埋在土里了。
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一种“天才病”。事实上,更多的孩子只是在受苦,80%的自闭症患者比Bias综合征严重得多,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性的。对于这些患者来说,“能够成才”大概是天方夜谭,“能够独立谋生”已经是治疗的最高目标;但对于少数病情较危重、智力表现较差的重度自闭症患者,不得不将治疗目标降为“能够自理”。
但是,不应该责怪父母。这种病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。自闭症是病,卫生部门要管;自闭症的治愈之道是教育,教育部门要管;自闭症是精神残疾,残联应该管;自闭症造成很多社会问题,民政局也要管。但在目前的情况下,全社会对自闭症的关注和支持还远远不够;相反,误解和伤害比关心和支持更加普遍和深刻。
成立一年,一个会议带来了王和Ed,一个会议带来了大量的种子客户。孙梦麟说,“我觉得这两个会议就是为了我们。但随后,孙梦麟马上发现自己多虑了。在几乎没有营销的情况下,彩鹿的康复网站12年来一直比肩。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——不仅在中国,在世界范围内,自闭症康复机构都太少了。
即便如此,很多家长最初参与治疗时,还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态度。所以有些自闭症干预从业者觉得最难沟通的不是孩子,而是家长。
形容残联平时的样子也不为过。但是在这仅有的一层楼里住了将近100人……不,大约200人。正是在周三下午,在座的家长普遍在30岁左右,让我担心他们的出席情况。
跳过令人震惊的成长史。2016年,疾控中心数据显示,美国自闭症发病率高达1/68,而中国按最保守估计为1%。也就是说,中国至少有1000万自闭症个体,其中包括200万14岁以下的儿童。这意味着自闭症不再是一种罕见的疾病,而是一种常见的健康和社会问题。
从一个创立12年的公司,我依然看到“任重道远”这四个字。
我们走过不同的教室,走过集体辅导区和个别辅导区。“这桃子真好吃。你喜欢吗?要不要?”既然你已经拼完了,你不应该把拼图还给我吗?这样的基本社会指导,每个老师都在重复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自闭症干预场景:为了让自闭症孩子知道“名字”的意义,每次老师叫他的名字,他都跑在他身后,为他表示赞同;跑回来,一直叫,后面跑。重复这个动作数百次或数千次。
在漫长的医学历史中,自闭症的发病率一度被认为只有万分之二到万分之四,是一种罕见的疾病。
第四个错误是父母的忙碌。如前所述,由于老师无法一直陪伴孩子,家庭教育的干预成为重中之重,这就需要家长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——这对于中国的工薪族来说几乎是奢侈的。随着孩子留给保姆和爷爷奶奶,孩子的人生前途会越来越暗淡。
但孙梦麟最终还是和ed签了三年的合同,条款包括“收入的10%”。事实上,孙明·孟林的决定是正确的。Ed不仅为彩鹿奠定了科学的诊疗方法,还培养了本土人才,为彩鹿建立了庞大的自闭症病例数据库。这个数据库让国际学术界刮目相看,也让七彩鹿成为自闭症研究的世界领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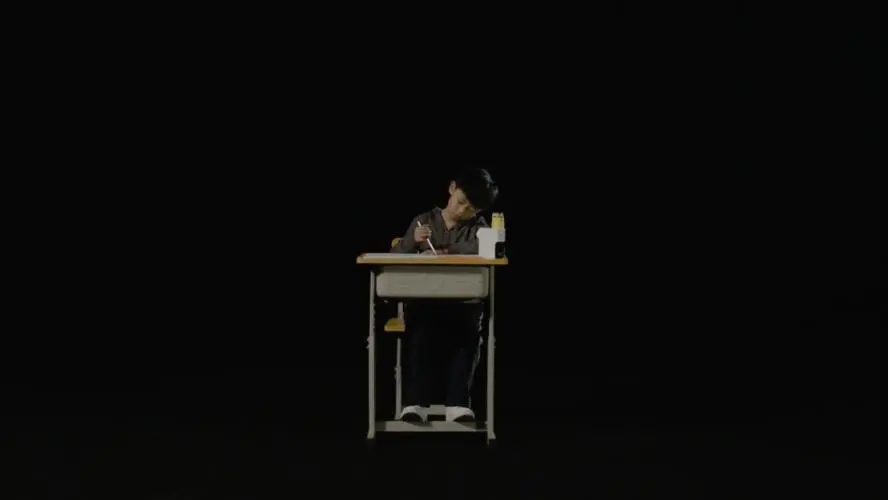
- 发表评论
-
-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>>












